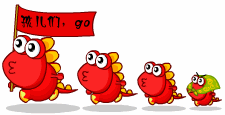原创:我的童年
阅读数:2009 |
回复数:4
|
本帖最后由 aaa1040486897 于 2012-3-8 21:12 编辑 神木特殊教育学校 杨宇 世事就像一盘正在下的棋,人们就是这盘棋里的一个个棋子。人的一生就是棋盘里的棋子在不停地寻找自己的位置。在我们零零星星的记忆里,生在六、七十年代的童年是枯黄的,酸涩的,但也是别有风味的,叫人难忘。我曾以为这些恍如隔世的记忆,随着岁月的流逝,必然将淡忘在记忆的长河里,谁曾想近些年来,这些记忆却越来越清晰,就像刚刚发生的一样。如陈年的老酒,越来越有滋味了。我虽然潦倒半生,一事无成。但回想自己走过的路,想起自己的童年,把一些散碎的回忆拼凑在一起,还是满有滋味的,让人回味无穷。 我生长在一个有一百多人口的大家庭里,我的父亲有弟兄六个,我们又有弟兄五个,所以,有了记忆以后,家里就非常贫困,因为人口多,父母挣得公分少,家里总是饥一顿、饱一顿,很难盼到穿新衣裳,一套衣服老大穿的小了,老二、老三接着穿,一定要穿的再也不能穿了,才扔掉。 在我小时候,父亲不知多少遍地给我讲同一个故事,使我了解了我的祖辈的过去。据说我的老爷很有才能,家里开了一个酒坊,是远近有名的财主,后来,和别人起了纠纷,打起了管事,可他又不懂送贿赂,被人家算计了。据我爸爸说,还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公堂对话,县官收了贿赂,要断我老爷输,但证据不足,要屈打成招,我老爷就是不服,虽然多次被打得死去活来,但就是不签字画押,在公堂上大喊“冤枉”,县官也束手无策,又一次过堂,县官看见我老爷在大堂下面的砖地上,拿着一个钉子抠砖缝子,县官大声喊“你在下面干什么?”,老爷说“我在挖糊涂虫。”县官说:“胡扯,世上那有什么糊涂虫!”老爷说“眼前不就有一条吗?”县官说:“在哪里?”老爷说:“你不就是糊涂虫吗?”县官恍然大悟,原来是耍笑自己。又是一顿好打,但总究是证据不足,把老爷放了回来,老爷的名气更大了。我家的生意越来越好。 后来,慢慢的有钱了,毛病也就多了,老爷染上了抽大烟的恶习,没有多少年,就把家产抽光了。没了本钱,酒坊也倒塌了。紧接着我爷爷也抽大烟,还没等老爷下世,家里就一贫如洗了。到了土改时候,家里连吃的也不能保证了,彻底的成了贫下中农,这也是我家土改中贫农成分的由来。如今,一切的一切都烟消云散,只留下一座大的院子,一个很深的酒窖,还有一面笨重的大酒锅,在无声地诉述着这些往事。证明着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。 留在我朦胧记忆里的,是天地之间太阳是那么红,村子里的树嫩绿嫩绿的,村子周围沟沟里经常流清清的泉水,美丽极了。大人们无论穿什么样的衣服,胸前照例是缀着像章的,被太阳一照,明晃晃地刺眼。最奢侈的就是有一个黄挂包、一顶黄帽子。如果,穿一身黄军装,就更牛逼,不知会多么帅气。那时候,人都吃不饱,我家一般就是在一个大铁锅里煮一锅照见人影子豆子饭。没等睡觉,尿几道早已饿了。记得有一次,我夜里做梦,就是赴宴席,满桌满盘的肉呀,香喷喷的,于是抄起筷子就吃,可待要张嘴时,却醒了,才知是梦境,懊恼得不行。有时候梦里的“运气”好,是可以吃到嘴里的,起了床便第一个告诉娘,娘就惶恐地问,咽了?答:咽了。娘说,吃不得,那是鬼饭呢。心里便怪怪的,没了兴致。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,大凡都知道,那个时候,虽然吃不饱,可人一个个的都打了鸡血似地劲头很足。村里的生活,一般是白天上工,夜里开会。走在村里的路上,墙壁上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大字报,好看极了。会是批斗会,没有电,但有灯,雪亮雪亮的罩子灯,被直直的竹竿子挑起来,于是满场院里仿佛铺了层荧光粉。我们这帮小孩,是牵着大人的手去的。人很多,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,一脸的严肃,我们觉得莫名其妙,眼看着有人被绳子绑了,掐着脖子提溜过来,然后又被丢在台上,像一坨闷泥。几个穿着绿衣服的人,挽着袖子,举着拳头,向着人群大声喊:打倒四类分子杨二秃!台下群声附和,气势逼人。 我很纳闷,少不更事地琢磨,为啥要打倒“杨二秃”,是因为他没头发吗,于是便下意思地抬起手来摸摸自己的头,头发硬得扎手,这才放下心来。 于是,我仔细听才明白,原来他偷了队里的两个南瓜,被抓住了,成了四类分子。 如果每天夜里开批斗会,白天保准满村静悄悄的,斗人的累了,四类分子也累了,而我们不累,我们几个人相约了扎一种网子,如果不开会,我们几个一准是挨家挨户地捕麻雀。那时是冬天,麻雀们白天到处觅食,夜里就栖在房檐下的墙洞里,只要掐亮了手电,被光线照定的麻雀一动也不动,我们就抄了网子照准了罩上去,麻雀受惊飞出来,一头钻进了网子,我们只需要顺着墙一拉,麻雀就端得是逃不了了的,用手握住了,使力朝着地上一摔,麻雀就匝开了毛,流着血水,抽搐着死了。 如是这般捕麻雀,如果运气特好的话,这一晚我们可以捉到十几只。慌慌地,跑到谁家的灶房里,悄无声息地烧开水煮了,半生不熟地吃,连细骨都嚼碎了咽下。真好吃呀! 后来复课,我们只得去上学。生产队给布置了一孔窑洞,桌凳都是家家户户凑回来的,也是老师在台上讲,我们坐在下面听,到了冬天,我们穿的棉裤单薄,坐在凳子上,隔了棉裤都觉得冰冷,屁股就麻麻的木了。上课真是无聊透了,有时候听着听着眼皮就管不住了,上上下下地开始打架,勉力想睁开,却没力气,就头一歪,枕着胳膊睡着了,醒了,涎水流湿了书本。 现在,窑洞已经荒废了,我每次回家,还忍不住站在破败的被荒草包围的窑洞前,看上几眼。 那时候,上学没有作业,谁愿意写作业呢。我们放了学,把书包一丢,就跑出家门疯去了。除了捕麻雀,夜里还真的没事可做,就相约着去生产队的牛棚里捉迷藏,最好的藏处就是放牛草的草堆里,整个房子里铡好的草堆得满满的,钻在里面,非常难找。玩累了,我们就讲故事,听同伴云山雾罩地瞎扯,我们常讲的,无非就是妖魔鬼怪故事,瘆得人浑身颗颗粒粒的,却依然在堵着耳朵听。为了自己讲,我们就想办法,弄到故事书,并啃下来,给同伴讲。如今想想,我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,完成了我的语文学习的启蒙。 若干年后,我只身告别了这样的生活,一个人跑到了镇上的中学读书,然后又去了县里。后来读了榆林师范,参加了工作。 客观地说,我们这代人,在学业上的确是耽误了不少光阴,且又生在一个物质相对匮乏的时代,似乎是不幸的。然而,我们却在不幸中拥有着特有的难忘的童年。和九十年代的儿童相比,我们的童年别有风味。我们的童年也完整而有趣,我们并不是是“被耽误的一代”。 |
 发表于 2012-2-24 05:15:24
发表于 2012-2-24 05:15:24

 微信
微信 收藏
收藏 推荐
推荐 无聊
无聊 提升卡
提升卡 置顶卡
置顶卡 沉默卡
沉默卡 喧嚣卡
喧嚣卡 变色卡
变色卡 抢沙发
抢沙发 千斤顶
千斤顶 显身卡
显身卡